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并理解抑郁症的确不外乎是一件好事情,起码让真正深受抑郁症折磨的患者们能够及时意识到自己的情况,并前去就诊。
身边的人也对抑郁症患者们多了许多了解和尊重,从某种程度来说,当更多人能够对抑郁症患者具有同理心时,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也随之降低了。

为什么现在却对“抑郁症”这个词及概念的大肆流行抱有警惕心甚至开始隐隐担忧了呢?
这源于大家对抑郁症以及其它精神疾病更多层面的了解。
抑郁症概念是否被滥用?我认为抑郁症的概念是被滥用了,而且是被严重滥用了。
抑郁症概念被滥用,不只是网上“口头诊断”的问题。
更令人胆寒的是,抑郁症已经在耳濡目染中,全方位的渗透进我们的文化体系和话语体系当中,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植入未经审视和检验的“抑郁症概念”:
1,2,3......符合这几条症状你就是抑郁症啦;
确诊抑郁症别慌,这里有治疗方案1,2,3......
赶紧码上...
01
越来越多心理健康的人在抑郁症概念的暗示下,最终真患上了抑郁症。
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曾在20世纪早期写道:新的医学知识露了许多疾病,都是人们从未听说过、此前从未被注意过的。
人们越来越“担心自己健康方面,哪怕最微小的变化”,因此反而“更容易生病”现在抑郁症概念泛滥,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过于宽泛,甚至可以说是定义不清,唯一能把抑郁症(疾病)和抑郁情绪(正常情绪周期)区分开来的标准就是“症状是否持续了一个月”。
这种含含糊糊的概念导致抑郁症几乎可以套用在大部分人身上,这就导致大部分身体不适都能和抑郁症沾上边……
现在我们在探讨一种精神疾病的起因时,一般都会从现代医疗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抑郁症也不例外。
从生物进化层面,
也就是人的大脑层面来分析现如今抑郁症大流行的起因,我们可以发现:从古至今,人的大脑结构变化不大,短短十来年更不可能发生任何重大变化,所以抑郁症大流行与人大脑的变化相关性不大。
从心理层面,
也就是人的心理结构层面分析抑郁症大流行的起因,我们也可以发现,它虽然不像大脑那么稳定,却也是漫长岁月里逐渐定型的,除非遇到极其重大的刺激事件,短期内也很难巨变。所以,抑郁症大流行与人的心理结构相关性不大。
从社会层面,
最后从外部环境层面来探寻抑郁症大流行的起因时,我们有了惊人的发现:社会文化对精神疾病的影响巨大,即“抑郁症”概念滥用产生的文化暗示效应。
诚如理查德·戈登( Richard gorder)在《进食障碍症:解剖社会流行病》( Bulimia eating Disorders: Anatomy of a Social Epidemic)一书中指出:
“一旦进食障碍变成一种人们广泛认定的“行为问题”,那么原本已经有着情绪障碍或者焦虑问题的人,又或者已经有病态心理模式或者人格发展脆弱的人,再或者曾遭受性虐待或者家庭成员中有过体重失控问题的人,他们都更倾向于采取这一被文化许可的行为来应付内心的重重痛苦。”
抑郁症也如此,
一位香港的精神科医生也在实践工作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况:
他分析的患者群体均在20世纪90年代记录在案,他发现后半部分所记录的那些病人明显更多地属于这种“我也是”型的病人。(即当某一疾病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解,传播后,但凡有心理痛苦的人们便趋向于用这一疾病标签来表达内心痛苦,借此获得更多人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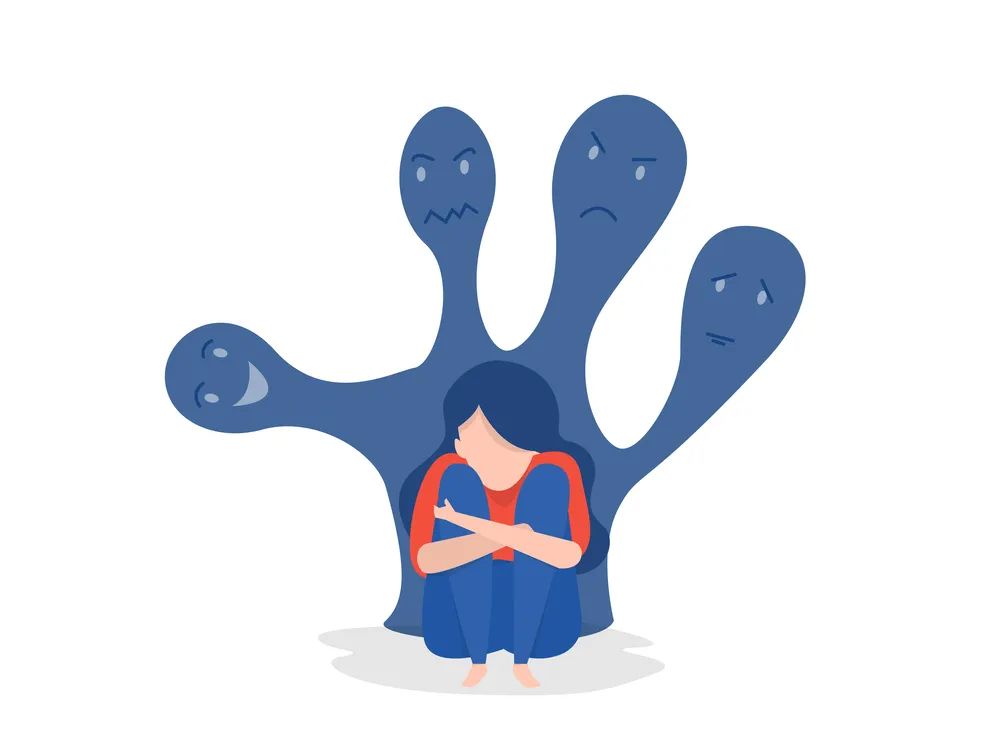
这位精神科医生发现,一旦某种精神疾病的寓意被人理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就开始用这种行为来表达她们尚不清楚的焦虑和痛苦。
当我们有种文化的气氛或氛围,就是专业人员,媒体、学校、医生、心理学家全都认可、支持并且到处谈论并传播关于某种精神疾病的知识,那么那些已经带有那种广泛的心理状态的人就可能被触发,有意或无意地以这种疾病的病态作为一种表达内心冲突的方式。
总而言之,人类的潜意识总是试图用其时代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自己情绪所受的痛苦的。
当抑郁症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那么越来越多的人用抑郁症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之苦也就不足为奇了。
抑郁症概念的滥用如海妖之歌一般,诱惑着越来越多的人步入抑郁症牢笼,让抑郁症像流行病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中华大地肆虐横行。
02
文化塑造疾病体验,它可以在无意识中塑造病人对自身疾病的体验。
当我们身患某种精神疾病时,内心往往被模糊不清的困扰情绪和冲突所纠缠。
这种内在折磨我们的东西往往超越了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这就导致我们在尝试表达自己内心痛苦时一再遭受挫折。
这就导致病人在无意识中选择当下医学诊断并认可的症状来解释内心的痛苦。
或许会有朋友问了:
这样来看,抑郁症概念的泛滥是一件中性事件,甚至帮助那些难以表达内心痛苦的患者能够更清楚的表达症状,并获得周围人对他所承受痛苦的理解了呀。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话语体系下,我们对抑郁症的主观意义和症状体验有很大差异。
比如同样看到“抑郁”这个词,
日本学生联想到排名前十的词是:雨,暗,担忧,灰色,自杀,寂寞,考试,抑郁,疾病,劳累;
美国学生联想到排名前十的词是:悲伤或感觉悲伤,孤单或感觉孤单,低落,不开心,有情绪,低沉,灰暗,失败,苦恼,焦虑。
松贝博士研究发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美国学生的个体独立意识较强,日本学生相较于美国学生,其自我少一点独立的个体感,更多是与社会或自然背景的交织,如学校,公司,天气。
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对抑郁症的症状体验和存在的意义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形容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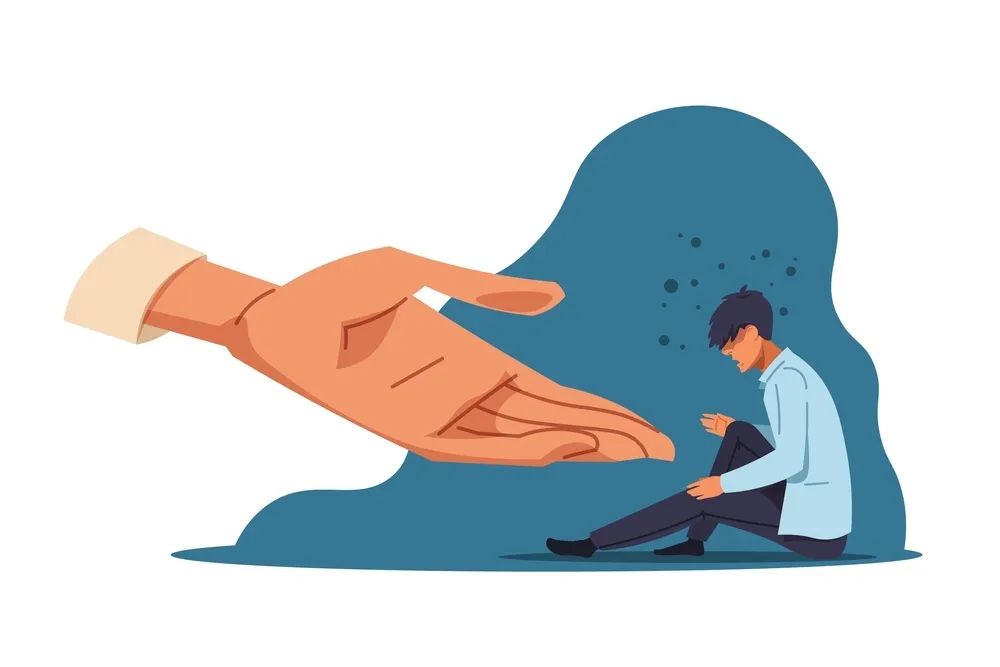
其实在我们亚洲文化里,我们对深度的悲伤包容性是很强的。
比如: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
在我们的文化里,深度悲伤的感觉非但不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力量和卓越人格的标志。
但现如今抑郁症的流行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文化对这种心理感受的包容性,导致我们的心理对这种情绪感受的承受能力大大降低。
正如科迈尔所说的:一个文化里被视作人格增强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就是病态甚至带着挑衅味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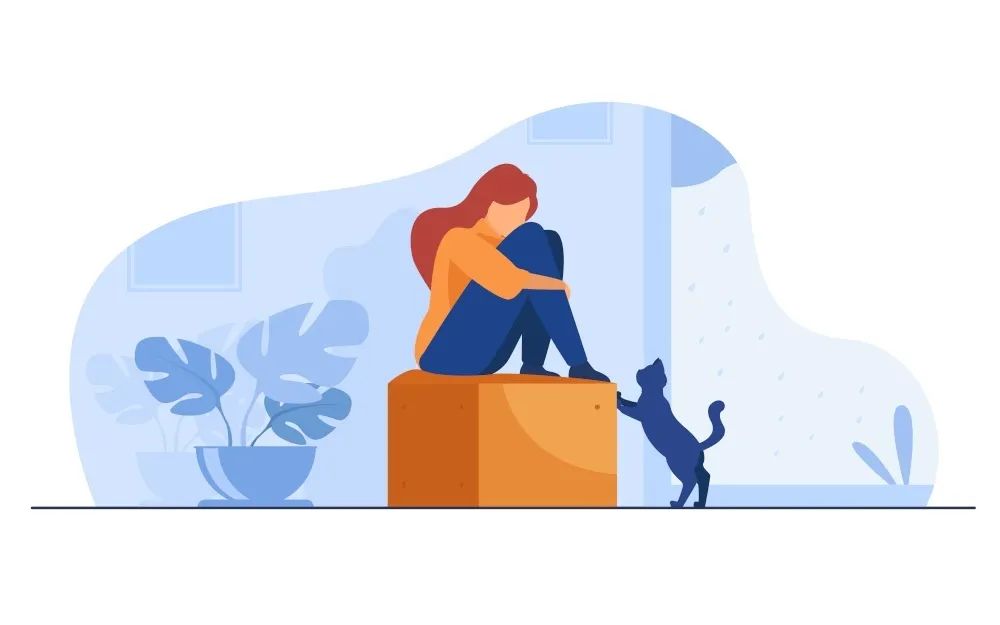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心理疾病失去了它原本最真实的面貌,给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诊断治疗设下重重迷障,导致他们很难顺藤摸瓜,找到心理疾病的根源,对症下药。
如果发觉自己的抑郁情绪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并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最正确也是最合适的做法就是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去检查诊断,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依靠科学、专业的治疗手段,尽可能地在治疗的黄金时间里治愈。
切勿自行在网上寻找相关资料给自己诊断或寻求他人的“口头确诊”。
当抑郁情绪已经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幻想着靠自我调节或者是一些活动来对抗抑郁症,因为这时候抑郁症已经处于病理性质的状态了,单纯靠着自我调节已经无法起到作用,充其量只能当成治疗阶段的辅助手段。
毕竟,自我调节再合适也不能代替治疗。
